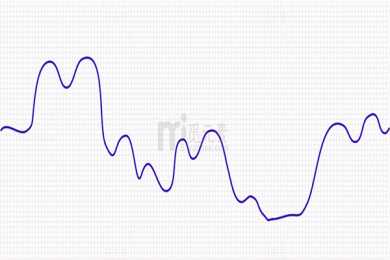李翎 | 水陆仪起源的理论思考
 admin 2024-12-04
1
admin 2024-12-04
1
内容摘要:随着图像学研究在历史与艺术史学科的深入,水陆画进入学者研究的领域。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流行于宋代的水陆仪与保存下来大量明清的水陆画的起源在哪里?笔者针对目前有关水陆仪是源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说法,论证以祭祖度亡为目的水陆仪与水陆画的源头可能是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而不是来自印度的佛教。
原刊:《东方论坛》2018年第1期。
引言
一、水陆仪是什么?
通过文献记载来看,至少从宋代开始,中国的佛寺、道观流行一种度亡施食法会,佛、道皆称之为“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是什么?水,指的是水中的亡者、陆,指的是地面上的亡者,水陆法会就是在一些特别的时间里,为那些死于水中或陆地上的亡者进行超度和施食,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和各种鬼怪。在举行仪式时,要请神、降鬼、摆放祖先(亡者)牌位。因此,这个仪式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诵仪文、唱腔和“舞蹈”外,还需要有请降诸神鬼的图像。神鬼图像,从形式上大致分两类,一种是可移动的板画、卷轴、小画片,另一种是不可移动的寺观壁画。晚唐两宋时,寺观建筑群中往往单建一个水陆院,或者将弥陀院作为水陆院,在此绘制诸鬼神画壁和举行施度法会。
笔者参加过几次现在佛、观的水陆法会,结果令人非常失望,那就是诸神图像的几近消失。
现在佛教的水陆仪,在一般寺庙中几乎不再使用图像。道教也只简单地摆放三清(有的仅是单清)、然后再加一个鬼王(救苦天尊),正一派的话,会再摆放张天师的像。云南剑川法会,只在结界的地方悬挂一些简单的图像,降神时法师手持符木,在空中书写神的名字即可。至少在清代甚至民国时还存在的丰富水陆图,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于是,这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水陆仪或者说宗教文化中,图像的意义到底有多大?通过今天的调查,可以让我们对宗教图像在仪式中的重要性重新思考。研究以往的图像,没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是在回望历史。那么,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其重要意义,在于思考中国神鬼文化是如何发展与变化的,以及宗教活动中仪式与画像哪个重要?何时何者变得更重要?
二、水陆仪的起源
(一)理解中国宗教现象
讨论水陆仪的起源,事实上就是搞清楚水陆仪的本质,这样,才能弄清这个仪式的源头与佛、道的关系,而不能仅仅通过历史传说和现存文献,因为文献也会说谎。
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现象,自然要把水陆仪放在广义的道教里面讨论。它反映的是“道”与“术”在宗教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宗教文化史,主要就是道教与佛教的演变史。道教或是显流、主流或是巨大的潜流,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虽然,从教界和世俗的角度看,佛教是显学,道教比较沉寂,但忽视道教的影响,将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佛教。现在学者的研究方向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执意认为是水陆仪源于佛教,一些学者则认为水陆仪是道教的,在图像上孤立地去分辨道教水陆画还是佛教水陆画。学者之所以这样作,是由于一个明显的现象:在佛教相对兴盛的地区和来自佛寺的实物,水陆画的主尊以佛像为主,比如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区的寺观壁画。而在道教兴盛地区,比如四川、湖南、福建的水陆画则以道教神为主。这样区分佛、道有没有意义?笔者认为,意义不大。研究水陆文化,尤其对于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宗教现象,学者时刻要提醒自己把握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原本就是一个人、鬼、神杂居的世界观,佛菩萨与天官地鬼,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都是这个世界的神鬼,它们是没有宗教界限的。庞杂的地方信仰系统,将佛、道、地方诸神全部纳入其中。这时你看到的佛不再是佛教意义上的如来、你看到的千手眼观音也不再是佛教密宗意义上的千手眼观音。如果以什么经或仪轨的对应来研究这种具有地方性质的“术”,显然出力不讨好,也不能正确解读这些神鬼图像在地方信仰中的真正意义。
对于水陆画研究,当然最令人不解的是所谓“南水陆”、“北水陆”的划分。所有的地方道术、神像样式,都有地方特征。中国如此之大,并且也不是一个狭长的地理分布,只以南北来分,显然会产生歧义,它完全不同于学者型的禅学南北分宗理论。遍地神鬼的宋明时代,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甚至一条街道与另一条街道的神像都会存在差异,如何以南北分之?比如河北怀安的昭化寺水陆壁画与南宋宁波出口到日本的样式几乎相同,而郑振铎收藏的水陆版画与宝宁寺和昭化寺的壁画又不同[1][i]。地区的时空概念与文化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无法回答佛像是什么样的一样,我们只能说初唐广元的佛像样式或盛唐长安的佛像样式。“道”与“术”的关系是辩证的,同时,道相对稳定,而术会产生丰富的变化。
[1]参见郑振铎收藏明刻本《水陆道场神鬼图像》,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水陆仪式流行的地方,其神祇会体现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就是说一些地方、家族神怪可以随时加入其中,如何根据一个什么“仪”来套用活生生的地方神画呢?这个问题涉及到目前几乎空白的古代画工作业方式的研究。由于话语权的问题,这些民间工匠不被文人所齿,古代中国工匠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传承方式的记载几乎是空白。我们只能想象当时作坊中的画稿可以保留较长的时间,可以保持某类图像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但另一个问题是民间作坊很多,流动性很强,一个作坊中的画工可以在西安画壁,也可以流动到成都。画工之间保守自家图像不外流的特点,以及随时补充破损图像的随意方式,也使画像即使在同一个区域也不会相同并不断地产生变化,某个委托者特殊的个人诉求也使画工的神像组合产生变更。比如到了明代,五通神已经进入山西的水陆画中、妈祖也出现在北京的水陆画中。但这种流通现象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福建泉州一带水陆画中经常出现的扶箕和杯筊形象就没有在四川等地发现,至少可以说不流行。所以,现实的宗教现象非常复杂,不会有一个标准去套用,要具体图像具体分析。
(二)中国佛教的“道教化”
中国历史变革于唐宋,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不仅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清政治、经济的变革,还可以发现非常显著的宗教变革。如果以目前学界的共识来说,佛教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在唐代之后就彻底中国化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古代哲学、历史文献、科学技术以至于“迷信活动”,都可以纳入广义的道教范畴。严格地说,中国本土的道教是没有边界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鬼神观就是道教形成的土壤。历史上幸存下来的各类文献,从广义上讲,都可以归入道藏的范畴。中国民间广泛活跃的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广义的道教多神崇拜的不同形式。因此,抛开精致的知识分子佛学,所谓的佛教中国化,毋宁说是“道教化”。这种远离知识分子玄学式的普及化了的民间佛教,在宋代之后,其核心已经道教化。如果一个农夫说他是信佛的,很可能他是道教徒,他的神龛中供奉的是太上老君、龙王、孙悟空和一个抱着童子的观音娘娘,民间生动的宗教崇拜活动大多只是套着佛教的外壳。传统贵族式的宫观道、丹道,也演变为民间大众广泛参与的生老病死式的宗教关怀。中国自汉代以来,各路佛道神鬼,经过洗牌,在宋代之后,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神鬼系统,佛陀、菩萨已经不再是外来的佛教圣者,而是中国的神明。明代成书的《封神演义》[ii]、《西游记》[iii]等小说最好地诠释了宋代以来民间对这种神鬼世界的整顿与重新排序。今天的学者再用佛教、道教来归类庙中所示神像,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神像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神鬼世界,很难说是佛教或道教的。并且依笔者对佛教的认识,大乘佛教中许多的佛、菩萨本身就非常可疑、来路不明。如果想说明水陆仪中一些神像与佛教渊源的话,首先要弄清佛教史和造神史,看清他们的是佛教的还是婆罗门教的,因为这两个教派在印度完全不同,但许多后来出现的佛教神却来自婆罗门教。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学者对于水陆仪研究出现的偏颇,可能有几个因素导致:一是文献话语权误导;二是忽视了文献保存的偶然性;三是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即一叶障目。当然,我们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只能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如果固执地在一个单纯的领域内去解析中国宗教艺术、自说自话,则无效且非常危险。
[2]参见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著、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张海洋校《洁净与危险》,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19-141页。
[3]参见美国学者巴瑞特著《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曾维加译,齐鲁书社2012年出版,第5页。
(三)水陆仪的起源
1、佛教说还是道教说
如佛教仪文所示,佛教僧人编造了梁武帝发明水陆法会的故事,为进一步加强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又编造了唐代瑛禅师对于水陆的重视。但是所有相对可靠的历史文献都指明这个特别的宗教活动可能始于唐末五代,广泛流行于宋以后。1007年宋真宗“梦”神人授意建“黄箓道场一个月”。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这一个月,非常有可能是农历7月,即中国传统所谓的“鬼月”。同时这也似乎告诉我们,这个持续一个月道场,有可能是非常高规格的一次参杂着祭祀佛道诸鬼神、类似后来水陆仪一样的斋会。水陆仪在宋代开始盛行,寺庙、道观都将这类法会称之为“水陆”。道教在唐代之前具有宫庭性质的传统“黄箓斋仪”,由于其繁琐性和过度的神圣性,被民间以祭祀“水”、“陆”鬼怪的简单仪式所代替。但是除了佛教关于水陆起源的传说和保存下来貌似佛教的水陆仪本之外,佛经、道藏都没有直接的“水陆仪”记载。只是一些水陆仪使用的图像,主尊往往是佛,但是由此,并不能说明水陆仪起源于佛教。被学者普遍用来证明水陆是佛教的最早材料是《益州名画录》对画家张南本的记载:中和年间(公元881至885年)“僖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于宝历寺置水陆院,请南本(张南本)画天神地祗、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也。至孟蜀时,被人模塌,窃换真本,鬻与荆湖人去。今所存,伪本耳。(伪本淳化年遭贼搓劫,已皆散失)”[4][vi],但事实上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首先,文献并没有明确说这些画是佛教的水陆。其次,从张南本所画的人物来看,完全是道家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鬼神而不是佛教的佛、菩萨。虽然画在一个“寺”的水陆院中,但是,并不能由此断定这堂水陆画就是佛教的。四川的佛寺非常道教化,有时候观也可以叫寺。由此涉及的另一个材料,就是所谓“眉山水陆”的原始材料,即1093年苏轼写的“水陆法像赞”。事实上,我们也并不能由此确定苏轼所赞是佛教还是道教的水陆画。但是可以明确的一个事实是,宋代的四川,是一个道教极为昌盛的地区和时代,而这种昌盛源于四川非常远古即流行的鬼神信仰,我们可以通过《山海经》找到这个传统。而道教一向注重科仪,即道、术不分家。道教科仪的主要目的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祭祖,所以“水陆仪”非常可能是由祭祀天、地、水三官而衍生的祭祖神鬼活动。当然,天神不在鬼列,对地、水之鬼的祭祀正是水、陆法会活动的核心。水陆法会的核心意义是祭祀祖先和各类亡灵,祭祖和鬼神文化是道教的传统而不属于佛教。虽然后汉出现有佛教的崇拜祖先类《孝子经》、《报父母恩经》,但这些佛经的“翻译”非常可疑。当然,最大的疑问是佛教的水陆文献,佛教僧人将水陆仪的起源附会到梁武帝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崇佛弃道的皇帝。但是,假如这个仪式与梁武帝有关,要注意的这个皇帝的“弃道”,这说明武帝最初是信道的,但为什么在继位的第三年“弃道”,学者猜测很多,目前尚没有明确资料说明。但一个事实是妄佛的梁武帝,却一直保持着与高道陶弘景的友谊。所以,我相信,武帝倡行的佛教中,一定夹杂着大量道教的内容与形式,也很有可能,这个武帝借用他熟悉的道教祭祖和度亡之法,在佛寺中举行过类似的法会,这大约正是传说的由来。至于水陆仪是否源于这个弃道崇佛的怪皇帝,是另外一个话题。
[4]参见黄休復撰《益州名画录》,卷之九第九页面。此印本收录于日本1987年《早稻田文库》。
水陆仪的另一个特点,正像从东汉张道陵开始时使用的方法一样,即仪式结束后要将使用的箓图烧掉。火,是水陆仪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佛教的水陆仪,在仪式尾声的时候,也要举行盛大的过火仪式,即将一些供奉鬼神的衣服、纸马和食物一把火烧掉。用火是中国宗教活动,或者说是祖先崇拜性宗教的传统。火是将世俗之物传递给彼岸和亡者的唯一途径,清明时节或先人祭日时,我们每个人大约都用这个方式给祖先送去冬衣或钱物。
[5]佛教中密教的护摩仪式,往往被学者认为是佛教使用火的证据,但这完全是婆罗门教的方式,不在佛陀之教内。笔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即密教与佛教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佛教进入中国,直到今天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这2000多年是在质疑中走过来的,虽然也有灿烂的时候,但总体来说,它的立足和发展比较艰难。我说的艰难指的是,佛教为了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进而适合老百姓的口味,只能不断地改变自己,不断地调整自己原来的尺度。所以非常可悲的是,在这种调整和所谓的弘扬过程中,外来佛教的权威感和神圣性一直在一点点丧失。最终以佛教在唐代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完成在中国的妥协和蜕变,这就是我们在唐宋之后看到的所谓中国佛教。所以,如前所述,与其说佛教的中国化,不如说是佛教的道教化,理解中国思想史是解释佛教中国化的最好途径。
通过大量记载的水陆仪材料看,水陆仪式可能最早出现在四川,这是非常自然的。四川在历史上一直是道教的根据地,唐代中原盛行的精英道教和宫廷道教文化也通过唐皇多次入蜀而官民结合。所以当时在四川,乃至长安和洛阳一带的中原,流行的水陆仪式应大致相同。但是随着地区性鬼神的不断加入,到明代以至于清代、民国时期,水陆仪和水陆画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地方性。所以,可以确定,晚唐具有浓厚道教文化的四川地区是水陆仪发生和传播的中心。
2、从话语权看水陆仪的起源
[6]参见王卡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6-61页。
现存两份有关水陆仪的文献是《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和《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以下简称《法界》、《天地》)。13世纪,南宋僧人宗鉴撰写《释门正统》,将仪文中关于水陆法会起源于梁武帝的说法收入其中,此说由是为佛教“正统”。两个水陆仪文也都如是说,甚至还可笑地说到因为唐代一个叫英禅师的神遇,使失传的仪文再度流行。显然这是中国上层佛、道斗争中,佛教僧人的一贯技俩,编造神话、推广神话,为当时的佛教造势,以对抗道教,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始见于北宋尊式所提到的“水陆”一词,其语境显然与水陆法会并不是一码事,而且尊式使用的这个词,很有可能来自道教传统。
现存《法界》,日本学者将之收于《《卍续藏》,这个本子由宋末元初浙江福泉寺僧人志磐撰写、经明代修订。另一个文献《天地》是没有入藏的明印本由北宋杨谔撰写,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宗颐向对此进行过一些删增,明代也再次印行。
是否收入藏中存在偶然性,与其是否重要无关,但这两个本子非常有趣。《天地》本显然是俗人、也有可能是道士编写的,编的比较早,至少在1095年前已经完成。并且按序中所说,这个本子在四川当时非常流行,明代再次得到印行。另一个本子是大约比此本晚至少150年以上,由一个见于记载的浙江天台僧人所写,明代也再次得到印行。在四川当时非常流行的前者,很难说只用于佛寺。晚出的《法界》,非常明确的是佛教僧人编写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天台宗僧人。这个由隋代智者大师所创、以《法华经》为中心的著名学派,它的影响由上层知识分子而广被民间,并且衍生出各种忏仪更是流行民间,其仪式不乏道教色彩,由宋末元初浙江天台派僧人撰写的水陆仪本非常正常,其中加入大量道教内容,或者直接改编自四川流行的道教仪本也理所当然。虽然,从文本看,这个仪式形式上是由僧人在执行,但是从行文和内容看,完全是一派道家行为。从开始的降神、请城隍等,完全运用了道教的存思、请神之法,与佛教完全无关。所以宋末元初,四川地区佛教强烈的道教化以及江南地区道教的流行使僧人志磐无意识地运用了道教的方式,或者干脆就是直接整理的一个佛教面貌的道教科仪文献。正如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对敦煌道教文献观察所得:在敦煌石窟寺中保存的很多道教抄本原本是被当作佛经收藏的[8][x],僧人使用道教文本、道士使用佛教科仪,是宋代之后民间宗教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中国宗教文化不设边界特点的一个反映。
[8]参见日本学者大渊忍尔著《敦煌道经目录编》(上)隽雪艳、赵蓉译,齐鲁书社2016年出版,第9页。
[9]参见LiLingandMaDe:收录于YaelBentorandMeirShaharEdited:
至此,我们还要强调水陆是佛教的吗?或者说水陆可能起源于佛教吗?水陆仪式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吗?
3、对佛教盂兰盆节的质疑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之所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盂兰盆节时,佛寺会举行盛大的水陆仪,而《佛祖统记》正是将梁武帝首发“盂兰盆斋”作为水陆仪之始。早在西晋或东晋就存在的《佛说盂兰盆经》似乎更是将水陆仪归入佛教系统最重要的证据[10][xii],但是这其中存在很大的疑点。
[10]日本学者在编辑藏经时将《佛说盂兰盆经》定为西晋竺法护所译,但在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却定为失译,现在一些学者也认为其是伪经。总之,这是一部存在很多疑点的佛经。
[11][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57页。
[12]同上。
如所周知,盂兰盆节是中国的僧人自唐代开始就执行的3个月夏安居结束后的七月十五日举行的施食祭祀活动,而这个时间正是中国传统的中元鬼节。这个秋收时节,人们舒展了劳作一年的身体,可以坐下来享受美食,一轮生命结束,万物在秋收之后,进入寂静的休息阶段。当然,在人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之前,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祖,要把崭新的收成首先献给祖先,这个活动叫“尝新”。所以,七月十五,乃至整个7月是中国人特别的日子。美国学者太史文先生非常敏锐地察觉到,安居结束与农时的关系。并提到:这个时候正值满月、季节交替、秋收、祖先转生,一切都在过渡到新的形式与万物更始相一致[13][xiv]。
[13]参见[美]太史文著、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信仰与生活》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页。
安居的缘起据《四分律》卷三十七“安居犍度”记:佛在舍卫国时,有六群比丘于夏月游化,结果暴风雨将僧人的衣钵、坐具、针筒冲走了,这件事受到世人的讥笑,笑话比丘们在大雨天里还到处游走。于是,佛便制定了“结夏”的戒律,即在夏天雨季的三月,要安居不再游走乞食,同时思考自己在这之前游走时所犯的过错。据说这是佛教安居的滥觞。安居之制,并非佛陀的创造,原是印度古来旧习,印度其他教派的僧侣都有夏安居的习俗,通过《四分律》卷三十七“诸外道法尚三月安居”可知。按印度的气候,夏季降雨频繁,不能游方乞食。因此佛教比丘在经历了被雨水冲走物具的事情之后,为避免再受“外道”的讥笑,也实行了雨季安居。按早期律典,在这个时间,僧人自己会寻找一个安静场所,接受饮食卧具供养,忏悔游行中所犯的罪业,并专注于策励道业。3月期尽,自恣日后再分散各地,游行教化。《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四记:以四月十六日为安居之始日,七月十五日为终日,翌日为自恣日。《摩诃僧祇律》卷二十七则以七月十五日为自恣日,也就是安居结束于前一天的七月十四;《大唐西域记》卷二、卷八所举之安居期为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安居时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古代印度不同地区历法的时间不同导致,但大致属于一个时间段。当然,对此玄奘也有解释,他说印度以星计月,不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差错,这个安居时间对应中国的农历就是五月十六至八月十五,别的说法是错的[xv]。由此,可以发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安居结束的时间,无法刚好与中国七月十五的鬼节衔接;二是安居结束后,玄奘以及之前没有任何材料提到跟着有一个大型的佛教祭祖度亡法会。
从以上记载看,佛陀虽然制定了安居之法,但并没有提到之后要举行重大的施食饿鬼活动,这完全符合佛陀之教法。而且,目前没有发现这个《佛说盂兰盆经》的梵文或巴利文本。
以笔者在印度生活的经历看,现在的印度无论4月、5月还是6月,完全无雨,而且非常炎热、干燥如火,5、6月因为高达摄氏50度的炎热连蚊子都消失了。印度的雨季,始于6月底月,大概可以持续2、3个月,即7、8、9三个月。这个时候,因为雨水的清凉,蚊子“复活”,会传播登革热。这个雨水时间,事实上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非常相似,即通常的暴雨来临是在阳历8、9月,即阴历7、8月。玄奘《大唐西域记》记安居结束于中国农历8月,那么就与笔者现在的经历一致。从纬度来说,印度的气候或者说雨季,从佛陀时代到现在,即使变化也不会相错2、3个月,只能说雨水的多少产生一些变化而已。可是,为什么古代佛教文献记载的坐夏是从4月开始呢?并且从《四分律》来看,4月虽然气候火热,但安居显然不是为了避暑而是避雨,可是4、5月根本无雨。那么问题出在哪?一个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学习了7年的中国僧人告诉我,这也是他的疑问,来到印度后得到解决。因为古代的印历与中国的农历,基本相差2、3个月!4月正是中国的6、7月!所以,如果按印度历安居始于4月至7月结束。对应中国的农历则是6、7月始,结束于9月左右,正是现在的阳历8-10月。对此,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八关于“菩提树”内容也提到:在菩提伽耶有肉舍利,每年在如来大神变之日将之示人,这个时间是印历12月30日,对应中国农历是正月十五。按玄奘的说法,中印古历,相差在2个月左右。如此,安居结束、自恣日之后的时间,与《盂兰盆经》所说的七月十五盆节完全对不上。并且通过文献看,至少在玄奘去印度的时候,还不知道印度有个盂兰盆节与佛教安居结束后的活动有关。
所以,从时间上看,印度佛教的安居与中国盛行的盂兰盆节,在时间的衔接上肯定有问题。笔者的结论就是,所谓失译的晋本《佛说盂兰盆经》,正如历史上许多学者认识的那样,非常可能是一部伪经。盂兰盆节,不过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味,借用中国传统的中元鬼节,以佛教的名义,在七月十五日广施饿鬼一并饭僧的重大法会。
三、水陆仪的研究方法
[14]关于庙堂仪式与图像的观看,非常感谢北京大学魏正中教授,在与他的对话中他的一些观点启发了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历史遗存,尤其是文献,对于今天的我们,很难据此判断它记载的是当时的真实文化还是作者或委托者的好恶。比如,一个古老文献的性质是什么,就涉及到我们在使用它时的态度和节制度。最典型例子是《山海经》,弄清材料的性质,才知道如何利用文献。书写文献的作者是什么立场?作者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撰写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考虑。这是对于现存历史文献而言,同时还要考虑到,找不到的记载并不等于那些事情没有发生。以二十四正史来说,它不会样样都记,而不见于记载的事件并非没有发生过。记载的偶然性以及文献得以保存下来的偶然性都要考虑进去。
结语
综上所述,水陆科仪,本质上是道教的活动,是道教宫廷性的祭祖、度亡仪式的民间化和普及化,是道教传统对于祖荫观念的强调,它与佛教、印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之所以留下来的文本看似佛教文献,其实是唐宋之后,佛教的世俗化,即佛教道教化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唐宋变革后,中国人神鬼观念在这一仪式中的体现。具体来讲,水陆仪的起源与道教古老的天、地、水祭祀关系更近。辨清水陆仪起源于佛还是道,目的是厘清事实,理解中国宗教现象。只有弄清这个宗教现象,才可以在这个思路下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i]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ii]许仲琳.封神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iii]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v]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张海洋校.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v]巴瑞特.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M].曾维加译.济南:齐鲁书社.2012.
[vi]黄休復.益州名画录[M].东京:早稻田文库.1987.
[vii]迭朗善译.摩奴法典[M].马香雪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viii]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x]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M].隽雪艳.赵蓉译.济南:齐鲁书社.2016.
[xi]YaelBentorandMeirShaharEdited:ChineseandTibetanEsotericBuddhism[M].Boston:
[xii]高楠顺次朗等.大正新修大藏经[M].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12-1925.(16).
[xiii]宗懔.荆楚岁时记[M].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xiv]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信仰与生活[M].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xv]玄奘.大唐西域记[M].钦定四库本电子版.
李翎,现任教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曾担任以色列国家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印度尼赫鲁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宗教图像学、藏传佛教图像学。出版专著译著12部、发表论文70余篇。
著有《醉舟醒语—宗教画纵横》、《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中国工艺美术史纲》(合著,第一作者)、《藏密观音造像》、《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之《西藏佛教雕刻艺术全集》第五卷《石刻》、《观音造像仪轨》、《佛典与图像—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佛教造像精粹》展览图录、《梵天佛地》(全8册,翻译第1卷、第3(1)、第3(2)卷共三册)、《佛教与图像论稿》、《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鬼子母研究:经典、历史与图像》等。
- 同类文章
- 友情链接
-






















![[海外翻译]后座体验如飞机头等舱!外媒试驾奔驰S600迈巴赫](/imgs/baidou-v2/upload/2026/01/16/09/ac3b406473f4467b16c539dddc2fc009.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