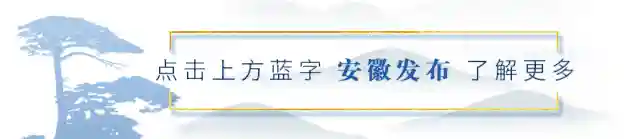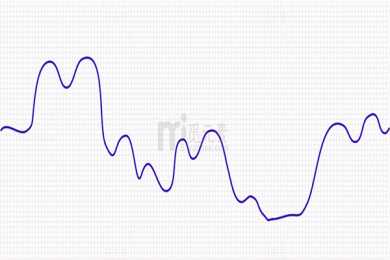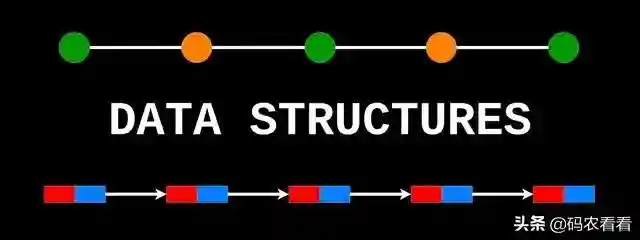郁达夫翻译过《京华烟云》吗?
 admin 2025-10-21
156
admin 2025-10-21
156
《京华烟云》原名MomentinPeking,是林语堂于1939年﹝49岁﹞所完成之作品,耗时一年,并为专心书写举家迁法。该书经过构思研究布局长达半年后,方才写作,写作期间历时一年。全书70万字,分3卷,共45回。出版后仅半年时间,就热卖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台北林语堂故居并未收藏到此月刊,但仍寻访到复印本,现以电子书方式呈现,希望可以提供读者更多林先生的相关信息。本收录共计六篇,请对照最下方页数,郁达夫已完成第一章及第二章第一节之翻译。其文字具有时代感,精炼流畅尚不足以形容,仅此献给喜爱林语堂及郁达夫的读者。
林语堂故居2015.10.21
唯须指出者,乃是自第6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起,该刊开始连载“林语堂原著、汎思译”《瞬息京华》。首次发表其“第一回”后,第7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第8期(1946年9月16日)、第9期(1946年10月16日)、第10期(1946年11月16日)、第13期(1947年2月16日)分别连载“第二回”,其后未有下文。但前后6次所发表之译文,仅为原作第一册《一个道家的女儿》(THEDAUGHTERSOFATAOIST)的第一章与第二章的第一部分的翻译。然则,从上述这一简短的叙述中可以见出,汎思译《瞬息京华》之发表时间,为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但众所周知的是,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也就是说,汎思译《瞬息京华》发表于达夫遇害之后。准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若是达夫译稿,缘何不在其生前发表?
早在《京华烟云》英文原作尚未出版之前,林语堂就已经邀请达夫担任此书的中译工作。1939年9月4日,林语堂自纽约致信郁达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嗣后语堂寄奉手订翻译参考数据二册及一定之订金(有说是五百美金,有说是一千美金,有说是五千美金,待考),达夫不久当即着手翻译。
次年,林语堂决定自美返国,飞赴重庆前夕,给达夫一信,彼复信称“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而且“想近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就排就矣。”(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6-337页)然而,此时《宇宙风》为避战乱,已迁至香港,可能达夫不知内情,因而甚为乐观,大开包票,此其一。
其二,由于种种我们至今无法获知的原因,《宇宙风》卒未刊出达夫的译文,但郁氏之翻译工作的确已经在进行,且不久将在南洋地区的报章上发表了。1941年11月16日,亲见过郁译初稿的徐悲鸿,给林语堂写信,称郁达夫已“译完大约三十万字,”而在《宇宙风》未能发表的译作,此时正在由达夫本人主编的《华侨周报》揭载,“彼已有十分之一,发表于此间《华侨周刊》者殆两万字,闻至来年五月可以全部译成。……(中为引者略)彼今在《》副刊编辑兼编《华侨周刊》,甚为忙碌,以弟观之,明年五月必不能完工也。”(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第88页)但此信中的《华侨周刊》,是徐悲鸿的笔误,应是《华侨周报》,其由驻新加坡的英国情报部门主办,聘请郁达夫兼任编辑。
徐悲鸿的这一记录还得到以下的证据的支持。首先是新加坡《》所刊《华侨周报》之广告显示,1941年8月30日出版之《华侨周报》第22期已开始连载郁达夫译《瞬息京华》,且署名“郁达夫”,并非笔名。(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第88页)其次是达夫当时的友人、左翼作家王任叔,亦曾表示《华侨周报》曾发表郁达夫所翻译的《瞬息京华》。(王任叔《记郁达夫》,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再次是与闻其事的郁达夫之子郁飞,也证实了此一发表记录。郁飞尝谓父亲听取自己的建议之后,决定在《华侨周报》发表译稿,“每期周报上都有一栏译文。女助理自然从旁斟酌文字。按说,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详注,他译此书决无难处。可是拖延近两年,终因大局逆转而只开了个头。”(郁飞《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新洲的三年》,《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
几十年后,郁飞还在新加坡最大之华文报纸《联合早报》撰文,希望搜集“《瞬息京华》的译文若干段,”以为“只要有那份刊物就能复印。”(方修、连奇编《郁达夫佚文集》,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综合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华侨周报》曾发表郁达夫译作,且其字数在两万(郁飞语)至三万(徐悲鸿语)之间,林语堂亦具悉一切,为构成今人发掘达夫所译《京华烟云》稿的三点重要之事实。
但是,同年12月27日,《华侨周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达夫译文的发表也随之再次夭折,从此成为林语堂、郁达夫及万千读者永远的遗憾。也因此,这一残存的三万字左右的郁达夫译《瞬息京华》,成为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极力搜寻的重要文献史料。去夏陈子善教授访台前,嘱笔者查访台北市立图书馆。原来陈教授数年前曾蒙林语堂之女林太乙见告,知林语堂全部藏书暂存此馆,郁达夫译作手稿及《华侨周报》或亦厕身其中,但此后林氏藏书及遗物却全部移交林语堂故居。待陈教授来台,遂于会议、讲演之暇,驱车上阳明山,访问故居,试图找到这份发表件,希望给即将迎来的郁达夫一百二十周年诞辰送上一份最好的礼物。
此故居兴建于1966年,由林语堂亲自设计,融合中西建筑风格,颇为别致。林氏晚年曾在此居住十年之久,直至逝世。因获政府资助,加之执事者苦心经营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遂能集纳全部林氏藏书、著作、手稿及其遗物,而向社会开放,不仅具有一般纪念馆所功能,可以招徕游客(来自中国大陆之游客尤其多见),亦构成一艺文活动空间(当地市民及团体亦可租借场地)。是日我师弟二人,无暇饱览风光,只逐一查检林氏藏书,费时甚久,然达夫译文仍如石沉大海,难觅其踪,不禁为之怅怅久矣。后陈教授作《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即略述此一因缘(陈子善《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文汇报》2015年9月26日第8版)不过,这是闲话了。
其次,译者竭力使用北京土语写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时常还不忘操持旧小说的习语,使之披染上一层章回小说之风味,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类似的表述,会出自达夫之手。如第二回末五段中,有四段话重复以“且说”此类旧小说“话头”开头:“且说姚老爷合家老小出门在途,……”;“且说众人顺着保定大道一天工夫赶到涿州,……”;“且说姚老爷一家开始三日途程,……”;“且说众人第四日响[晌]午稍许一歇,……”。这样的陈词滥调,岂不构成对郁达夫自谓的“对于翻译,我一向就视为比创作更艰难的工作。”(郁达夫《谈翻译及其他》,《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的反讽?
林语堂博士的英文原著《MOMENTINPEKING》是一本伟大的杰作,自出版以来,风行一时。本刊兹得汎思先生的合作,分段译出逐期登载本刊,以飨读者,汎思先生不仅译笔信雅,且对北平话下一般苦工,故于书中人的对话,神态身份,描摹尽致,译风别具一格,敬希读者留意。——编者
我们知道,也正是在对郑陀、应之杰译本的长篇讨论之中,林语堂道出了自己委托郁达夫翻译此着的全副设想:“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而作为理想人选的郁达夫,不仅中英文俱精,还能掌握地道之京话,可采京话翻译,其译品因此颇有望成为《京华烟云》最权威、可靠的译本。另一方面,语堂对翻译的语言问题之重视,也可从上述感言中尝鼎一脔。
事实上,作为此一译事赞助人的林语堂,作为曾获得过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文学家,对翻译的语言问题重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京华烟云》甫一出版,听闻国内有翻译出版消息,语堂当即发表重要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其后又表示:“我不自译此书则已,自译此书,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郑陀、应之杰译本以其“未谙北平口语”,且夹杂上海话,令语堂深表不满。考察其相关论述,至少包括如下重点:其一,在白话与文言之间,倾向于白话;其二,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强调口语为主,无口语则用书面语;其三,在众多方言之中,独独青睐北京话,为的正是其中有大量浅白清白之白话、口语足敷使用。简言之,林语堂并不希望对译入语(targetlanguage)——汉语——有丝毫的扭曲,反而希望破坏英文原著的语言结构、内在的意指网络,从而成就一上佳的中文作品。然则汎思的译本表现如何呢?
请举例以言之。汎思译文第二回第三段,介绍八国联军侵华、庚子事变之起因,谓“那端王欲使太后猜忌各国对其废立之举有意阻挠,故假造列国公使会衔照会,要求太后让位光绪亲政。太后不知情诡,乃遽信以为真,因见那义和团以驱逐洋人为帜,甚足号召一时,乃毅然决用之以雪同仇之恨。但有几个朝臣,却是深明大义,认为拳匪焚毁使馆之议,有违西洋惯例,乃极力谏阻。无奈均遭端王党徒谋杀。……”纯是文言口吻,极少口语,甚且,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就连一个十岁小女孩的思想意识,译者也要大笔一挥,以半文半白、迹近文言的口吻出之。如临行前姚老爷告诉木兰,已妥善安置历年所藏,但逃难归来后,是被人刨去,还是仍属于自己?都在未定之天。这时,木兰“同时又得了一个教训”:“正是一人有无福气只是命中注定。断非偶尔逢遇。而有福必有德,才能享受。凡应分享福之人,一瓮之水。见之变为银。其不应分享福之人,一瓮之银,见之化为水。”显然,这是以高贵典雅的语言风格重写一少不更事的女子的片刻思绪,全然不符合其身份、语言特征。
试看原文:“,orfochi,wasnotsomethingthathappenedtoamanfromtheoutside,,,jarsofwaterwillturnintosilver;andforonewhoisnotqua1ified,jarsofsilverwillturnintowater.”在这里,叙述者试图运用自由间接思想(freeindirectthought)这一叙述策略,讲述一个关于好运、福气的古老的东方哲理,虽然可否出自一个少女的头脑仍不免让读者生疑,但在这部“太像外国话”的英文原作的上下文中,相近的句法、文法、腔调,都保证了它至少拥有相对稳定的节奏,而显得不那么突兀。可在汎思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高贵化(ennoblement)的翻译取向之下,原作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和创造性、复杂性既无法体现出来,作为小说背景的文言的叙述,也无法与小说人物对话的口语之间联系起来,形成内在的一致性。
更有趣的是,编者按语极力褒扬译者对北平话下过功夫,但汎思的译稿中却充斥着不少“假摩登之欧化句子”。且看汎思译作第一回开头:“话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停住一队骡车,有的排过街外沿着大佛寺粉红围墙一条南北夹道。”这是对下面这句话的忠实的直译:“ItwasthemorningofthetwentiethofJuly,1900.ApartyofmulecartswerelinedupatthewesternentranceofMatajenHutung,astreetintheEastCityofPeking,partofthemulesandcartsextingtothealleyrunningnorthandsouthalongthepinkwallsoftheBigBuddhaTemple.”又如姚老爷出场时形容他“好似提防被人不定前后左右猛然一下子打过了来一个模样。”而其原文是“thebody……readyforasurpriseattackatanyunsuspectedmomentfromthefront,theside,orbehind.”这里的中文翻译,也同样是十分机械的直译。
当然,这并不是说直译本身有问题,恰恰相反,好的翻译不免要混用直译和意译(思果《翻译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3-14页),但看上面所引的这几句话,要一口气读完实在都很困难,更遑论达旨与否。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它们都是不常见的中文长句,其中第一句有三十二字,第二句二十一字(这一点,我们当代人似乎可以接受),第三句二十五字,也是近代以来屡遭讥评的“欧化”句式。提倡白话文学的新文学家,虽然大率使用过“欧化”的长句,但语堂对此却深恶痛绝。他认为,“句法冗长者,非作者愿意冗长,乃文笔未熟,未得恰当文语以达其意而已。”(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因其深知,典范的中文表达,当以简洁、凝练为要,而且,无论中文、外文,总要求“用字须恰当,文辞须达意”。
郁达夫
既然确定一篇作品是否出自郁达夫的手笔——特别是那些未署名的作品或用其他笔名发表的作品是否出于郁达夫手笔,是要调查研究,从多方面来论证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单凭自己主观的设想或者不切实的旁证,宣称某一作品是郁达夫的佚文。(陈松溪《关于郁达夫抗战佚文的辨认》,《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诚哉斯言,发掘、整理近现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文献史料,皆须综合辑佚、辨伪与考证这三方面的工作,而不必如俗语所谓“拣到篮里就是菜”,轻易判定某文当属某人之散逸文字者也;至于整理,则须严格遵守古典整理规范与作业程序,“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梁启超:《立宪法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页)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故居发表此一译文之前言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当时的上海有诸多粗陋的盗印及滥译本”(故居方所依据的或是秦贤次、吴兴文编《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林语堂卷》(《文讯》第21—31期,1985年12月—1987年8月),其所录1949年之前《京华烟云》中译本只三种,皆系上海出版者,其疏漏无须赘述)其实,此书在四〇年代的上海、北平都有译本,至于究竟有哪几种是盗印、滥译,翻译史、文学史和出版史领域的研究者们都还在研究,在未作出可靠的结论之前,似不可一概否定,厚侮先贤。另,或可补充的是,至1940年,日本也已出现三种日译本,但全然删削原作中的抗日救亡思想(施建伟:《〈京华烟云〉问世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实不敢令人恭维,当年耳闻此事的达夫,就曾建议林语堂,不必抢时间与此一较短长(郁达夫:《谈翻译及其他》,《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
至于前言交代此事之背景,将林语堂委托郁达夫翻译的时间记误,且引用了两处富有争议性的记录,即其所付订金金额与英文原著初版时之畅销资料,似皆是不必要的疏忽,应予一定之注意。
二零一六年春末改订于沪寓
- 上一篇:易说错的10句英语,你能说对几个?
- 下一篇:武汉大学2020年考研复试分数线公布!
- 同类文章
- 友情链接
-